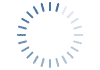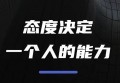未曾看见极光,可心中有流星划过
简单的,我只是能听见从薄薄鼓膜传到大脑的风林声。
裹了层厚厚的棉袄再与它融为一体吧,在不大冷了的天气,这样我可以洗涤心灵的一切冗余;
我可以用我黝黑的双眸把它描绘的洁白无瑕,我可以用双手捧住它,看它一点点变得透明,一点点在我的还算温热的体温里消失殆尽;
缩回手,掌心残留的凉意蔓延到指尖后,它会用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与我同在,告诉我它的名字永远,永远叫作雪花。
双手插进冰冷的口袋,佐似这世间仿佛只有我一个人是炽热地生活,借给我永久不散的欢欣,在茫茫大雪里,我会用永久的矗立去报答。
在北欧森林,在冻的通红通红的鼻腔里会孕育生命,即便是呼出一小团一小团白气,我也在此刻存活,褐色绿色的树,连尖顶也堆积雪了,素白的,素白的,请借我以火去点亮。
就像是未曾看见极光,可心中有流星划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