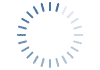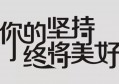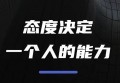我捻满园春色入酒入尘,独留我醉意绵绵
我眼见窗外的满园春色淌过冬雪夜幕的溪流,逃过夏秋的欲坠山色,独留下旧雪中一树的摇曳,窗花惊鹊稚嫩背部的弧度驮起远山的太阳,小巷行人的面上和着暮冬夹杂的透明水渍,混着岁月的光华与霜雪熬成一碗淌水似的温柔,直至漫过眼角的固执,在人间留下一坛满襟酒气、流转烟火。
我总爱看山间朝霞与暮云眉间的淡愁欢喜,被那一绵不经意光华描成淡白的晓月,爱看暗月涌动下的那一树树繁花,忽闪出一腰的风情与柔韧,使人醉意绵绵。
偶尔慵懒的躺在藤椅上小扇悠悠,想着春色总比夏景来的柔和,我眼中的春闹没有肆意招摇的清风,也没有始艳其浓媚的喧闹,在我看来它好似总是清淡,偏安于一隅的瓦上檐角,偶尔露出一点淡绿,却不言语。
偶尔恰着绵雨点点,便要去郊外踏青。
我之前见过正值暮冬时节下的苍茫四野,鸟雀落下痕迹,也见烛火惺忪最终沦为灰烬,本来不抱着多大期待,只想着散心,但在春意的熏染下,生命脉络历历可见,这景便不一般了。
从窗外看月,晚风轻撩起她淡白面纱的一角,独露出一截泛着点青的梨花枝,忽而就有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妩媚和冷清感,我敢说这种尚有迷离的风情,是春夜里独有的。就算即后便入了眠,梦里也都不住缭绕着美人香。
“春夜适合温柔的惆怅。” 正如这般模样,于我而言,春眠是梨花的淡白,是枝头晓月的冷清妩媚,是少年人兴兴轰轰的誓言信仰,但于我而言,我只是在卖花人那里,买得一枝醉意绵绵。